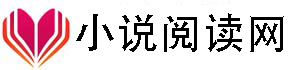40-50(26/28)
赋有限,这事裴元私底下跟妻子明说过,就如同自己在诗文上怎么用功也透着一股子匠气一样,谢文济的确不是个读书的料。这几年头悬梁锥刺股的在青松书院读几年书,考个秀才问题应该不大,再往后就不好说了。要是能开窍说不定还能考中个举人,要是不开窍,恐怕还得在科举这条路上磋磨好些年。
至于能不能考中进士,反正那天晚上谢九九箍着裴元的脖子死命追问,也没能从他嘴里逼出一句自己想听的好话来。
向来还算圆滑聪明的裴郎君在这事上显得格外迂直,怎么都不肯说半句哄人的假话。
一直等到谢九九缠磨累了,倒在裴元身侧脑袋枕在他腿上,叹息谢家这一代人看来又没个读书的种子时,裴元才小小声哄她:再耐心等一等,再过几年我给你生一个读书种子。
裴元这话说得一本正经,人却是不正经得很。
再之后谢九九便也没精力去想谢文济到底有没有天赋读书的事,只在被裴元托着一下一下挥汗如雨的时候,浑想着这人要是不读书,说不定还能去考武状元,这精力也忒好了些!
不过那些说到底也都是夫妻私底下说的话,明面上从来没有显露过半分。谢九九想得通,谢文济现在还不大,考不上进士也不能不读书了。
都说读书明理,他即便以后跟着自己学怎么当云客来的掌柜,肚子里也不能没一点墨水。又或是书读得多了心思清明了,以后有自己想做的事那都可以。
况且现在就不读书了还能干嘛?他的身体是比小时候好了,却也只是比小时候好。真把他带到云客来去,他还是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抗的弱鸡崽子。
到时候别干活没学会,反而天天跟着那些老饕酒鬼学移了性情。要是再学坏一点,到时候自己和娘哭都没地儿哭去。
所以不管是裴元还是谢九九,对于谢文济的安排都不着急。行不行的都先在书院里读着呗,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
谁知关如琅却不是这么想的,对于谢家一个小商户人家愿意花钱供一个读书人,他是打心眼里觉得是好事。毕竟外甥现在是谢家人,要是以后小舅子也能一起入仕,对外甥来说便是最天然的同盟和助力。
下午把客人送走,可不就捎带手把谢文济给叫过去了。
关如琅当年以二甲第八名入翰林院任编修,这个起点不可谓不高。随便挑拣四书里的句子考一考谢文济,就知道这孩子在读书一道上且还没开窍。
十四岁是不大,但对于读书人来说也不小了。要是这几年还不能开窍又一门心思只想考功名,那往后少说十来年都得吃些苦头了。
谢文济不好,谢家就没法好。谢家不好谢九九自然要多操心,谢九九整日围着谢家操心,自己外甥难道还能袖手旁观?这便是一大家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粗浅道理。
谢家很知礼懂分寸,关如琅为了姐姐和外甥着想自然也不见外,点拨谢文济之余也把他天资不够,这几年须得下狠功夫才有可能考中秀才的事给点明了。
“我知我不是聪明人,姐夫为何没同我把话说明白我也懂。好在关大人把话给我挑明了,要不然我还得被姐夫哄着,是个读书的‘尚可’,往后前途‘不可估量’的天纵之才。”
谢文济面上有些故作的哀怨,更多的还是在故意跟姐姐告状,‘你看你看,你丈夫看在你的面子上光知道哄我了,也不说实话。’
谁知谢九九一点点意外的神色都没有,还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对着谢文济。
张嘴想说什么又觉得说出来的话好像也不能安慰人,最后只得干巴巴的说了句:‘家里还有银钱供得起你,好好读书。’就再说不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