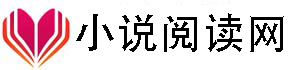50-60(10/48)
地盯着他,静默良久。久到一旁桌案上的灯烛都爆出噼啪声响,季泠仍旧愣愣地看着他,静静思忖。
“季泠,放、了、本、官,不然……”
季桓阴鸷的视线落在她
身上,薄唇张合,凝神思量的季泠并未听到他说什么。
“季泠!!!”
“放了本官!否则待本官出去,定然要撅了陆琛的坟——”
尚未待他说完,季泠抄起手边的佛经堵上了季桓的嘴,令他有口难言。
季泠捏着经书,稍稍使了些气力堵着他的口,拧起长眉深深地对上他满是怒意的眸子,缓缓道:
“阿桓,你喜欢辛宜,是不是?”
短短一瞬,男人暗沉的眸子中似乎有什么转瞬即逝。接着,怒火似从中喷生,眸底的熔岩几乎要将季泠活活吞噬。
但她如一樽坚韧肃冷的古像矗立在那儿,任凭熔岩焰火如何喷涌,都纹丝不动。
“你苦苦纠缠,逼迫她夫离子散,将她困于此地整整数月,夜夜同榻而眠,真的只是为了缓和你那所谓的梦魇吗?”
“季桓,难道你不知晓,你的别驾夫人早就死在了征和二年邺城之乱里,自那时起,你与她的夫妻之义,早已断绝。”
“现在活着的,不过是吴县小吏之妻,你堂堂尚书令竟然夺下属之妻?你不觉得,分外讽刺分外可笑吗?”
“我听闻,你向外放出消息,你的夫人并未死在邺城……甚至什么劳什子在佛堂清修五载,你觉得,世人都是傻子?”
“就连辛宜,她都不愿信,不是吗?”
“这回,就让阿姊再替你做一回主。你今后就在此好生养伤,莫要再去打扰辛宜了。”
“季……泠……”男人的身子浑然都在颤栗,一阵接着一阵得痉挛,心口的纱布被他挣得脱落,又涌一大片血。
一块碎镜捅的,本没有多深,但镜身薄脆,辛宜当初用力捅进季桓的心口时,镜身在里面碎得四分五裂。她还是好不容易,拿着镊子一点一点的从他心口拔出碎镜。
这等剜心之痛,他都不在乎,纵然躺在榻上动不得身,也丝毫不在乎自己的死活。
她这个阿弟,当真是对谁都狠。
季泠望着那滩浸润出衣衫的血水,眉心轻锁,抿唇思量着,看来季桓就算是挣尽全力,宁肯头破血流也要同她抗衡。
她叹了口气,拿下了覆在他下半张脸上的经书,侧身替他查看伤口。
“阿桓,爱一个人不是疯魔一般地将她囚在身边。辛宜她是活生生的人,她不是你豢养的鸟雀。”
“你为何从不思量一番,为何她拼了命也要离开你?为何她那般爱她后来的那个夫君?”
“若有朝一日你想明白了,也便不会再深陷梦魇,夙夜难眠。”
“巧、言、令、色。”他有些虚力得躺在榻上,眸光无力却又恼怒不甘,一字一句同季泠道。
“阿姊记得,你幼时养过一只狸奴,然那狸奴的胡须被二弟剪了去,它整日里闷闷不乐。”
“那时你担忧狸奴,白天黑夜都拿着鸡毛掸子逗弄它,还亲自捉了小雀与它,生怕它受一丝委屈……”
“你想想,你那时是如何对狸奴的?你也知你喜欢狸奴,便一个劲儿的宠它,哪也不去,整天都让狸奴睡你榻上。”
“阿桓,你待狸奴尚且如此,你现在又是如何待辛宜的?”
“阿弥陀佛……若非那件事,阿母也不会死,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。”
“你既然心悦辛宜,便不该如